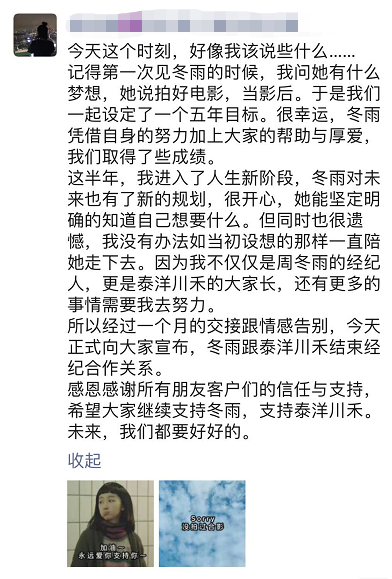“假如观众席里坐着一千名青年,他们手里就等于握着一千把利刃。我想,我得打造一个足以对抗千把利刃的舞台。那就是我的使命。”蜷川幸雄说。
手无寸铁的蜷川幸雄(1935—2016),一路荆棘丛生,直到去世前,他还在与这个世界、与新旧群体、与自己战斗不休。半个多世纪的导演生涯,逾百部奇崛作品,从地下戏剧到商业戏剧,从日本本土到国际舞台,他不断挑战规训,却始终遵循内心。80岁时,他还想重新开始,鲜衣怒马,壮思纵横。成长,是其毕生的原点。
《身毒丸》:火·童话
《身毒丸》被公认是蜷川幸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由寺山修司、岸田理生编剧。剧情并不复杂:身毒丸少年丧母,终日含悲忍痛、怀念母亲,不能自拔。父亲买来歌伎抚子以作继母,身毒丸对她始终心怀敌意,一番死生离合,终与抚子冰释前嫌,执手偕老。这么个“相爱相杀”的故事,在今天的我们看来,仍是一部“危险”之作。但是,外媒从《身毒丸》这枚“毒果”里触到了古希腊戏剧的脉绪,品出了莎士比亚的神韵。
开场,舞台顶处,一排电焊火花四溢,音乐却清冷忧伤。全剧就此定下基调,是童话,也是残酷。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做如是观。”并非具象的铁道,永不停息的驿站。男女老幼,拖家带口,或肩挑手提,或驱轮往复,满台市井影像,如游魂逡巡,极缓极慢。不知生里梦里,不知现实虚幻,不知当下过往。身毒丸紧握已故生母的照片,穿破拥挤的时空,无人相识,无人相应。卖面具的工匠与身毒丸家的女佣,以欢快的民间说唱,介入并间离于剧情,是叙述者,也是预言者。那匠人单为活人制作面具,因为活人的面目总是千变万化,只有死人不会假装。蜷川以日本传统能剧的笔法,给当下勾勒出一幅虚假孤寂的浮世绘。
父亲领着身毒丸,去戏班解散后的歌伎中“选”一个母亲,重组一个“幸福完整”的家庭。身毒丸虽不情愿,却无意中与一妇人一见恍然。就此,抚子以继母身份,带着养子千代,走进新家。但一瞬间,身毒丸眼中的“焊花”熄灭了。那不是他所要的那个人,他要的是谁?
抚子不甘仅是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,她向父亲求子遭拒。四人玩纸牌“凑家游戏”,但是三张“母亲”牌都攥在身毒丸手里,偏无人问津,游戏无法进行。呆板板、硬僵僵的一个“冒牌家庭”。“母亲”一起始便是缺席的,那也不是抚子要做的那个人,她要的是谁?
身毒丸有一只蓄养“切发虫”的玻璃瓶,企图让它剪去抚子的头发。抚子有一只盛满“希望”的小漆盒,拼命也不让人打开。因为受到身毒丸的辱骂,抚子打了他。因为抚子擦拭身毒丸生母相框时,他发现生母的脸“消失”了,打了抚子。
樱花童谣声声唤,上穷碧落下黄泉。身毒丸向面具匠索要了一面可以穿越到地下的“镜洞”,跳了进去。这却不是爱丽丝的“兔子洞”,也非“目连救母”的置换。这幕地下幽冥奇观,与地上市井百态对照,梵呗声声,烛船摇摇,各种失子的母亲—教母、后母、生母、养母,疯狂奔走嘶喊,连抚子也张牙舞爪地出现了。众“母”围猎着身毒丸,炼狱般“爱”着他。
一场臆梦吧。身毒丸一定不能接受,无论意识与否,从光里到暗里,“母亲”在他心中,渐行渐远,如实说,被遗忘了。抚子,是一道光,一捧火,已摄入他的刻骨铭心。
身毒丸打翻了抚子的“潘多拉”小盒,空空如也。这个“盗火者”,生生撞见了抚子的失落与失望,就必须为他的双眼付出代价。抚子诅咒着身毒丸,以虚拟夸张的敲钉动作,不断举槌挥向代表他的十字架,歌队附从,如群魔狂欢。每一根钉子,啄食着身毒丸的眼睛,他盲了。碎纸纷纷,如樱似雪。
两年后,抚子等候千代放学回家,将一件屋子的玩具模型一把扫进了垃圾堆。失明的身毒丸却戴着抚子的面具,身着抚子的服装,截杀了千代。千代死了,因为身毒丸是无可替代的;父亲死了,因为身毒丸是无可替代的;因为身毒丸对抚子而非“母亲”、亦非“继母”的“爱”,是无可替代的,是独有独占的;因为那一眼花火,他也杀死了从前的自己。
父亲坟前,身毒丸与抚子重又照面,一同忏悔。教人想起《简·爱》。身毒丸撕碎了生母的照片。摘下面具,扔掉冒牌,抛弃名字,祛除心障,身毒丸长大了,成熟了,他复明了,也复活了。“复活”,正是剧名《身毒丸》的别称。
《哈姆雷特》:血·祭礼
蜷川幸雄在执导《哈姆雷特》的场刊上写道:“我想创造的并不是旅游伴手礼般的‘日式《哈姆雷特》’。我要穷尽根干,而非枝叶。莎士比亚不仅是欧洲过往文化的结晶之一,同时也质疑着自己的现在。”蜷川的质疑,无非两个层面,一是过往的“哈姆雷特”能否成为今天的“哈姆雷特”,二是日式的《哈姆雷特》能否成为世界的《哈姆雷特》。这是我们排演任何西方或异国经典时都要打的一场遭遇战。在蜷川,任何艺术表现的“主义”,不过生成于其充沛排荡的直觉之中。
蜷川导演该剧,情节完全尊重莎士比亚原著,舞台结构则设计成19世纪日本贫民窟的两层长屋,破败荒凉。人物造型以现代为主,欧日合璧,兼有日本明治和欧洲宫廷的风格。服装以大色块耀眼夺目,如新王克劳狄斯与王后乔特鲁德的红、哈姆雷特的黑、奥菲莉亚的白、福丁布拉斯的蓝。老王穿日本传统将军盔甲,女士着西式长裙,男士则上身西装长袍、下身日本裤裙。跪坐即日式,剑斗则英伦。蜷川玩转魔方。
剧中,哈姆雷特布排戏班,试探老王如何为新王所害的“戏中戏”,历来为人称道,这是全剧的重大转捩。蜷川错彩镂金,全盘“日”化,却毫无鄙陋针脚。他竟奉以“雏祭”和歌舞伎的大餐,明艳恢弘地展现了一场谋杀。
雏祭,亦称女儿节、偶人节,以“雏人形”来庆祝节日,乃明治以后普及日本全国。“雏”即是人偶娃娃,水上流放或家中陈饰雏人形,是一种袚褉行为,为的是除邪去秽、祝祷平安。雏人形的摆设,极其严格,一般分为七个阶级共15个娃娃,按高低依次为:第一阶是天皇和皇后,第二阶是三名宫女,第三阶是五人乐队,第四阶是两位大臣,第五阶是三名仆人,第六阶是小型嫁妆家具,第七阶是牛车、笼、轿子等。
这场“戏中戏”之前,以一段能剧色彩的哑剧导引,之后,绿橙黑三色幕布拉开,红光倾泻,一座巨大的红色七层祭台端现眼前,所有歌舞伎演员装扮着人偶娃娃,各司其职、各就其位。天皇与皇后从第一阶拾级而下,庄穆从容,诉说着忠贞与守护。天皇小憩之际,一位大臣从第四阶伺机而至,毒杀天皇并公然篡位。看到此处,克劳狄斯愤而离去,乔特鲁德惊惶失措。—顷刻间,祭台坍塌!众人鼠窜!
一群小小的人偶,放大了等级秩序的荒唐;可作传代嫁妆的吉祥物,暗淌着看不见的鲜血;承载祈福的供台,成了表演者和观剧者的祭台。谁也无法置身度外,所有人的结局都已写好。这一刻,哈姆雷特豁然长大,他必须采取行动。这一刻,我们也会质疑,蜷川导演的到底是日本剧还是西方剧呢?并不重要。他漂亮地实现了日本传统文化对莎士比亚“命运”主题的偷梁换柱和深层转译。这不是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,是蜷川立于剧场之外,在战略而非止战术上的胜利。我甚至可以听见蜷川在操纵这幕悲剧背后的笑声,叛逆而冷峭。
东方民族的主流文化里,鲜有超越感的“忏悔”这个精神维度。像儒家主张“忠恕”,推己及人,非常现世。明治以来,日本人以西方文明经营功业,以儒学修身齐家,以神道教安驻灵魂,以佛教濡润美学。这种复合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。从日系《身毒丸》到莎翁《哈姆雷特》,蜷川对忏悔场面的构筑从来用心。祭台之后,克劳狄斯来到井台,他一边忏悔,一边打水,洁面,褪衣,袒露,洗浴,自笞,当头浇淋,披衣彳亍。这场戏简直动人之极。但这个僭位的王叔越发身不由己,越发一意孤行。哈姆雷特延宕了复仇,他那无法出鞘的利剑,只得化作无法自控的毒舌,啃噬着母后的身心,扯断了她遮羞的全部床帏。这是“他”以攫取和决绝的方式,索要“她”的忏悔。
奥菲莉亚自沉了;其兄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决斗,双双中毒剑而死;乔特鲁德误饮毒酒身亡;哈姆雷特临死前刺毙了克劳狄斯。玉碎宫倾满城血。“蓝色”的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莅临,但这个准备继承丹麦王位的少年,并非我们预想中的英姿勃发,他半身赤裸,瘦弱忧郁。他下令点燃隆重的皇家礼炮,抬出哈姆雷特的遗体。然则,礼炮并未响起,无声无息。二楼立着福丁布拉斯王子,一楼睡着哈姆雷特王子,他们在世界的边缘如是相逢,似一场未完的成人礼。切光。人性是否真的能在血污后洗蜕澄明,仍然是个未知。
《武藏》:剑·寓言
搜览蜷川幸雄的作品库,《武藏》是其难得罕见的一部喜剧,编剧为井上厦。它也许不是蜷川最有“分量”的作品,但可能是最有“意思”的创制。这似乎也是一个关涉复仇的戏,但与《身毒丸》《哈姆雷特》旨趣迥然。在蜷川导演的话剧《武藏》中,你若想看波澜壮阔的史诗剧、魔幻诡谲的武侠剧、坚韧不拔的励志剧,都注定扑空。《武藏》不是英雄主义的鸿篇巨制,毋宁说,它更像一台饮食男女的群口相声。
那场岩流岛决斗,本是人言言殊、扑朔迷离,《武藏》却并不发挥想象、大做文章。日中正午,武藏与小次郎摆开架势,对峙片刻,武藏突然发难:“这场比试,你已败了。” 兔起鹘落,小次郎倒地。惊鸿一瞥,非常滑稽。便知,这出戏,醉翁之意不在“武”。

《武藏》
故事揭幕了,也无猎奇可言。六年后,一个夏日,镰仓一座小庙宝莲寺落成,七人在此先后聚首:大德寺长老泽庵宗彭,剑术大师柳生宗矩,宝莲寺新任住持平心,担任建造工作的武藏,本寺大金主木材商阿舞和文具商乙女,以及前来寻仇的小次郎。小次郎甩给武藏一份长卷决斗状,指责他当年偷奸耍滑:武藏姗姗来迟,小次郎目对烈日,武藏的木刀比他的太刀长;约定三天后,再决高下。
如此规定情境和豪华人设,大家有钱的出钱、有力的出力,斗智的斗智、斗勇的斗勇,阴谋诡计加刀光剑影,好戏不是自然来?没有。《武藏》的主要情节可称作“三日禅”,以寺庙回廊为主景,以说法、参禅为契机,以狂言、能剧为穿插,以人物经历为噱头,复仇的危机一再被稀释,鸡零狗碎、插科打诨地奔到剧终。
这么说,会不会低估了蜷川的段位?“三日禅”的重点,也不在参禅本身,而是三次“梦游”。
小次郎下战书当晚,我们没有见到他和武藏如何各思对策、磨刀霍霍,看到的却是阿舞和乙女在表演狂言《蛸》,讲述一位行脚僧将一只乌贼的怨灵超度成佛。两人绘声绘色、穷形尽相。为了不让小次郎和武藏二人提前决斗,平心、泽庵、柳生先后将小次郎、武藏和他们一起绑成“五人六脚”。小次郎痛说孤儿家史,武藏斗嘴逞能自负,柳生唱着能剧梦游,七人牵牵绊绊、磕磕碰碰,跌爬滚打、扭作一团,令人捧腹。这场戏是对《蛸》的夸大。次日坐禅,柳生讲演能剧《孝行狸》,说的是狸猫之子为父报仇,要找兔子决斗。可巧,乙女正父仇未报,武藏、小次郎和柳生三位剑术高手都在,学武良机不容错过。众人先是劝解、推让,不觉相互学习,终从“团体操”演变成集体“华尔兹”。忽然间,四个宿仇浪人闯寺,手无缚鸡之力的乙女竟然“秒削”一人左臂。众人震惊,又不料乙女刀刃向己,为仇人包扎伤口。是夜走禅,平心、泽庵说法,道不可冤冤相报,当灭贪嗔痴“三毒”。怎奈武藏、小次郎冥顽不化,一语不合就剑拔弩张。这是对《孝行狸》的揶揄。
第三日前半夜,平心说法,小次郎戴着狐狸面具入场。狐狸在日本被视为稻荷神沟通人神的信使,佩戴“狐面”便是希求获此神力。“狐面”常见于能剧演出。阿舞哭诉歌伎身世,她曾与皇家有一私生子,拥有第十八位皇位继承权,那就是—小次郎。何以为信?阿舞取出半块手镜,恰与小次郎的半块“破镜重圆”。众人目瞪口呆,小次郎昏死过去。小次郎是不是皇子不重要,根本上他是一个缺乏内心力量和自我确认的被放逐者。
子夜梦呓,小次郎对武藏反复念叨着“第十八位”。武藏用扇子打醒小次郎,二人毅然终决。这是对“狐面”的击碎。枭鸟啼鸣梆声紧,寺庙隐去现竹林。青烟变幻中,剧中其他五人及四个浪人,皆着素服,相劝制止。二人不顾,挥刀相向,砍倒众人,却又死而复生。原来他们都是孤魂野鬼!止戈入鞘,众灵隐没。
武藏和小次郎握手言和,各奔东西。众人会面如常,平心说法依旧,一切周而复始,故事宛若无痕。竹林之战,直是“梦游”。岩流岛决斗,亦付笑谈。
如果,定要把《武藏》简单解读为个人恩怨须让位于天下公道的和平主义,亦无不可,一如剧名。然而,相较于蜷川其他作品鲜烈而激情的“高调”,《武藏》的“低调”是轻快而沉郁的。我不以为《武藏》的诙谐幽默等同于相逢一笑。
不妨作个拙劣的比较,《武藏》是一次对《十日谈》人文呼声的戏仿,对《七武士》英勇气概的嘲弄,对《罗生门》真相追索的消解。因为实际上,《武藏》架空了逻辑叙事,抹平了性格塑造,最终剥离了人物身份,从繁复走向简约,从故事走向寓言,从漫画走向抽象。这并不单纯地意味着蜷川的返璞归真,也许恰恰相反,他仍行走于冰火淬炼的锋刃。
蜷川幸雄:樱·自我
1985年,蜷川幸雄带着“给日本人看的”《蜷川麦克白》巡演至爱丁堡,当剧中勃南森林的苏格兰红松树变成东瀛风情的樱花树,一任向观众袭来,英国人看傻了眼。日本有句谚语:“花是樱花,人则武士。”生命短暂而灿烂的樱花是大和民族的精神象征。无论走得多远,蜷川仍是一个艺术家中的武士。但是这个武士,一出场便不是隐忍的臣服,而是不断的越界。蜷川的越界主要彰显在三个方面。
(一)剧场运动的反叛者
1955年,20岁的蜷川幸雄以一个业余演员的身份加入“青俳剧团”。明治以来,西化浪潮澎湃高涨,日本戏剧界先后出现了反对歌舞伎的改良“新派”,反对新派的西式“新剧”,以及反对新剧、更为激进的“地下戏剧”,即小剧场运动。“青俳”就是地下戏剧的青年先锋剧团之一。

导演蜷川幸雄
入行之初,蜷川便笃志要说“自己的话”,做“自己的事”。因不满于青俳的等级隔阂与矫揉造作,蜷川自任导演,创立“现代人剧团”,后不得已解散,再组“樱社剧团”,多年后又重建“蜷川剧团”。1969年,蜷川始以《真情满溢的轻薄》崛起于小剧场。同样以滑稽轻快演沉重主题,40年后的《武藏》,可谓是对这部成名作的冷却与超拔。
20世纪70年代,小剧场逐渐退潮,蜷川不再留恋。1974年以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夺取商业剧场。于是,莎士比亚和希腊戏剧成为他开辟欧美疆域的信使。戏剧的商业性与艺术性果真那么互为仇雠吗?艺术观念不同,伦理律条相异,语言的巴别塔永远高不可攀吗? 1983年,蜷川将日文演出的《美狄亚》带到希腊,三味线引沸了爱琴海。两年后,“樱花武士”《蜷川麦克白》造访英国,四海之门从此大开。 1997年,蜷川率团来到伦敦,这次的礼物是日本原汁却并非原味的《身毒丸》……
(二)东西美学的撞击者
《身毒丸》的悲剧,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的唯美派作品,如谷崎润一郎的《春琴抄》,琴师春琴与仆人佐助双双“盲目”,为爱情殉道;又如三岛由纪夫的《弱法师》,俊德五岁时遭遇空袭,失明离散,被人收养成人后,却拒绝与亲生父母和解,蜷川也曾执导此剧。这些作品都表现了日本文艺的物哀之美、幽玄之美。不同的是,《身毒丸》坚实地渗入了西方戏剧的赎罪主题。对于这类题材,我们惯常搬演的是,如妓女李亚仙为“励志”郑元和科考,竟将自己的美目剔去(《李娃传》);寡妇颜氏爱慕书生沈蓉,为全名节,竟将夜叩其门的两指剪断,获得朝廷“旌表”(《节妇吟》)。
我并不关心蜷川对东西古今各类视听元素的信手拈来,也不惊喜他对实体场面和虚拟意象的自由出入,甚至他作为一位“跨文化”鸡尾酒的高超调酒师,无论为人津津乐道还是频频争议,都非我的流连所在。能剧之于《身毒丸》、歌舞伎之于《哈姆雷特》、狂言之于《武藏》,既是面子,也是里子。蜷川将西方“罪美学”、日本“耻美学”及东方“禅美学”迁渡自如。
是的,内敛的幽玄美学与鼓荡的戏剧哲思,板眼凝结的表演程式与行动严密的结构法则,荣辱喜乐的道德期许与成毁得失的价值诘疑,以及阳春白雪的高蹈与下里巴人的通俗,热潮飞旋的裹挟与冷眼旁观的疏离,从来都是矛盾,但在蜷川的作品里,惟其矛盾,纵其碰撞而神思遇合,脱胎换骨。
对于蜷川而言,拓印传统或复制西方,都是邯郸学步。他所务求的是,深入历史传说和民间记忆的岩层,触摸那些戏剧的想象和体验的暗流,凿通人类心灵的隧道,震痛沉睡失联的颤音,触动当代观众的命运联结。
这条通往罗马之路,我们还走得非常艰辛。今年是话剧《茶馆》首演60年,《桑树坪纪事》首演30年,也是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膏药章》横空出世30年,我们能否从中明白一点,一边是灯塔在前,一边是缘木求鱼,所谓话剧、歌剧的民族化,所谓戏曲的现代化,远非以民族样式附着现代拼图,恰恰是要以现代思想澡雪民族艺术。
从莎士比亚、希腊悲剧到日本剧作与文学,蜷川重编日本传统戏剧的表演符码,深植于东西方文化的思想厚土,创造出叹为观止的舞台景观,形塑出独一无二的戏剧美学,被称为“世界的蜷川”。
(三)“以眼还眼”的挑战者
灿烂如斯,蜷川幸雄也从未躺在光荣榜上数指头。
蜷川曾在一次英文采访中说:“我一直在与我们文化中的缺陷作斗争—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‘自我’。实际上,我的艺术奋斗的核心便是找到这个自我。”
观众沉浸剧场,正是为了让其超越千丝万絮的“日常”,开示心底无言的“默狂”,这才是戏剧之于蜷川的存在。从《身毒丸》的炽热到《武藏》的冷静,作品强大的内省与涵容从未黯淡,蜷川不懈的否定与反思也从未断流。他同他的剧中人一样,仍旧时时怀着恐惧与质疑。他也害怕老,身体衰弱的同时会否带来对新事物的迟钝、对新观众的拒视?古稀之年,他觉得自己还得重生蜕变。他对记者说,“我不想成为一个令人厌恶的老头。”蜷川的一生,是一程行走利刃的注视,一场躁动不安的青春,有过凋零,但从未老去。
1972年的秋天,日本新宿地下室咖啡厅,一名愁眉紧锁的青年向他发泄着对戏剧的愤怒,满眼失望。那是在蜷川恋上戏剧的源头,永无忘怀。 “假如观众席里坐着一千名青年,他们手里就等于握着一千把利刃。我想,我得打造一个足以对抗千把利刃的舞台。那就是我的使命。”蜷川幸雄说。艺术家啊艺术家,你要永远仰望着那把达摩克利斯剑,在头顶,也在内心。